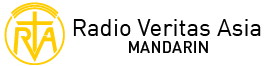【公教新闻】| 上海教务会议在亚洲和韩国教会史上发挥着重要意义

1924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中国教务会议,堪称“亚洲教会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我认为,这次会议对韩国教会意义深远”。这是圣座圣职部部长,韩国籍的余兴植枢机向在韩国首都首尔总主教区出席相关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们强调的。
11月15日,韩国教会史研究所、亚洲天主教史研究会以及西江大学神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第二届国际研讨会”,主题为“一九二四年上海教务会议的意义与影响”。远在罗马的亚洲教会在梵蒂冈的代表之一余兴植枢机视频连线大会现场发表了讲话。并深情回忆“去年这个时候,我曾出席在宗座传信大学举办的‘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研讨会’。当时,也有幸与上海教区主教成为新朋友”。在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主持下召开的“上海教务会议是中国天主教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契机,欧洲教会首次以勇敢的态度,迈出了将教会管辖权移交给本地圣职人员的第一步。圣座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终于通过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召集了中国天主教主教会议”。而在韩国天主教会的心脏,首尔总主教区明洞主教座堂灵修中心举行的这次研讨会,“将成为我们深入省思韩国天主教会历史根基、并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宝贵契机”。
余兴植枢机继续指出,“当时,刚恒毅总主教肩负着两项重要使命被派遣到中国。第一项使命是贯彻执行1919年教宗颁布的宗座牧函《夫至大》(Maximum Illud);第二项使命则是将《1917年天主教法典》适用于当地教会。这两份文件作为重要指南,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于混乱中的世界天主教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圣座通过这些文件,深刻认识到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重组内部组织使教会更能契合民族国家,并提出了面向非欧洲世界的新方向”。上海会议中所强调的“本地化”原则,“也对韩国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元山代牧区主教、天主之仆辛上院主教亲自出席这一事实,充分显示出这一亚洲性的转变对韩国教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本地化”原则“推动了韩国天主教会突破以欧洲为中心的模式,并在培养本地圣职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此,韩国教会得以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扎根成长”。也是“我们成功继承一九二四年上海教务会议精神的明证。今天,圣座积极倡导并践行刚恒毅总主教所开创的对话之路”。为此,圣部部长“衷心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能够重新审视上海主教会议的意义与影响,并成为确立韩国天主教会迈向亚洲福传中心的重要契机”。“我们的天主是进入人类历史并在其中行动的历史之主。让我们凝视那群以生命实践信仰的英勇的殉道者,也愿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代,在当今混乱的时代中也能立下志向,开创充满新希望的未来”。
另外,据韩国教会网站catholictimes.org报道,赵汉建神父领导的韩国教会史研究所与申义植教授领导的亚洲天主教史研究会,联合李振贤神父担任所长的西江大学神学研究所在首尔总主教区灵修中心共同举办了“一九二四年上海教务会议的意义与影响”国际研讨会。中韩两国专家学者们充分交流、探讨了中国教会在首届中国教务会议召开前的处境。那时,一直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传教活动下的“洋教”或“西方教义”面临着民族主义的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莱奥波德·雷博教授在《一九二四年上海教务会议的历史背景与意义》中指出,“上海教务会议是中国天主教教会史上的顶点与转折点,通过此次会议,中国教会为建立和发展教会体制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河南省安阳师范学院刘志庆教授发表了《一九二四年上海教务会议对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影响的概览性考察》论文,强调“上海教务会议通过积极任命本地主教、推动建立由中国神职人员管理的教区,为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韩国江原大学崔炳旭(保禄)教授在《上海教务会议与刚恒毅枢机的时代使命》中指出,“比约十一世教宗于一九二二年任命刚恒毅总主教为首位驻华教廷特使,他为推动中国教会本地化及强化独立地位,在外交与教育领域倾注了巨大心力”。韩国教会史研究所李敏硕(大建安德肋)首席研究员在题为《一九二四年上海教务会议与韩国教会的本土化——一九一九年《夫至大》通谕的颁布与平壤教区本地神职人员培养》的讲话中论证了上海教务会议对韩国教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原文选自“信仰通讯社”,有改动
Daily Program